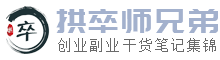樱桃里山菊谁扮演的
楼上的几位嘴下留情吧,这个演员叫张可,是赵本山徒弟王小虎的媳妇,看到上面有面跟她有关系全死啥的,那我估计本山传媒得死得差不多,包括主演沈春阳,白痴不要紧,就别那么无知,这部片子都是赵本山的徒弟和徒弟媳妇一起演,有人演好人,那就会有演坏人,没有她的坏,怎么会体现出沈春阳的好的,红红的善良,再说故事是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事,那会我们都比较穷吧,有这种表现我感觉也正常,农村人就这样,有时会因为一块石头吵起来,我不是贬低,我也是农村人,前段就碰到过,因为几块石头吵架,所以我很理解故事的一些情结,电视就这样,有人唱白脸,就得有人唱黑脸。。。
电视剧樱桃演员表
《樱桃》演员表:
1、 赵本山 饰 老歪脖子
2、小沈阳 饰 小舅
3、沈春阳 饰 樱桃
4、宋小宝 饰 葛望
5、齐如意 饰 红红
6、张家豪 饰 曲总
7、赵海燕 饰 葛母
8、红孩 饰 葛顺
9、张可 饰 山菊
10、蔡维利 饰 老钟
11、关婷娜 饰 大广播
12、王龙 饰 二狗子
13、李琳 饰 凤英
14、毕畅 饰 小丽
15、王亮 饰 李岩
16、路遥 饰 山菊爸
17、嘉玲 饰 山菊妈
18、王永会 饰 于老师
19、孙立荣 饰 李岩姥姥
20、小牡丹 饰 女老大
21、孙小飞 饰 寸板头
22、程红 饰 刘八
23、金燕 饰 盘发女
24、王洪利 饰 女老大爸
25、筱淑清 饰 女老大娘
26、雨婷儿 饰 香子
27、郭圣然 饰 葛东
28、黄巾倚 饰 曲娇娇
29、耿伊洋 饰 五岁红红
30、宛浩东 饰 五岁东东
31、杨冰 饰 侯文斌
32、赵丹 饰 胖丫
33、小飞龙 饰 三驴子
34、牧童 饰 香子妈
35、贺美玲 饰 嘎子妈
36、李淑静 饰 曲总岳母
37、王君平 饰 科大夫
扩展资料:
一、影片介绍
《樱桃》是本山传媒接档《乡村爱情小夜曲》着力打造的首部悲情戏,被誉为“赵家班”的转型之作。由沈春阳初次担纲女主角,宋小宝担任男主角,赵本山、小沈阳、赵海燕、红孩联合出演。由王振宏导演,2011年8月由黑龙江电视台出品发行。
该剧讲述了一个智障母亲樱桃(沈春阳饰演)与瘸腿丈夫葛望(宋小宝饰演)共同抚养弃婴红红,并帮红红寻找亲生父亲的故事。
二、赵家班介绍
赵家班,是小品演员赵本山在沈阳建立起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品、二人转团体。2009年大年初五,当日21时,赵本山在沈阳苏家屯的本山影视基地与众弟子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大拜师仪式。
赵家班成员:赵本山、李正春、路遥、张小飞、唐鉴军、王小宝、王小利、蔡维利、蔡小楼、王永会、张小光、波比·肯、闫光明、王小虎、王金龙、高明娥(女)、孙立荣(女)、贾小七、老臭、姜海军、程野、燕飞、杨冰、苏小龙、刘小光、小沈阳、张小伟、孙小飞、张凯、历小峰、程红、董三毛、宋小宝、小鹏飞、田娃、红孩、范伟。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樱桃
百度百科—赵家班
中国梦 歌词是山青水秀是谁唱的
张可。
张可,中国内地女歌手,硕士研究生,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独唱演员,世界环保形象大使。
2004年12月,应征入伍;2005年,参加全军文艺汇演;2007年,部队转业到中央音乐学院跟随刘海燕学习声乐;2009年6月,在河北艺术中心举办个人演唱会;2010年,获《华语民歌榜》冠军;2011年,MV作品《天下百姓》获得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
扩展资料:
个人经历
2007年,从部队转业,来到中央音乐学院跟随刘海燕老师学习,开始了为期两年的声乐专业学习。
2009年6月,在河北艺术中心举办个人演唱会,歌曲《天下百姓》在中央电视台与地方卫视多次播出。2010年,获《华语民歌榜》冠军。
2012年6月,她推出单曲《一个党员一面旗》 ;8月,录制了歌曲《幸福年年》 ;11月11日,举行首张主旋律专辑《一个党员一面旗》“献礼十八大”歌曲发布会,笑星博林今助阵。
2013年2月,发布歌曲《爱》;3月,发布歌曲《可爱的祖国》和《平易近人》;4月,发布专辑《飞起来》;10月1号,在北京成功举办个人独唱音乐会。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张可
张可的详细介绍
张可,翻译家、戏剧学者,1919年出生于苏州一世家,其伯祖父是民国初年曾任大总统府秘书长的张一麐,祖父张一鹏曾任蔡锷秘书。父亲张伟如留美学化学归国,与蔡元培之子蔡无忌共事于上海商检局。
张可读暨南大学时,受教于李健吾、孙大雨等,18岁时即翻译出版了奥尼尔的剧本《早点前》,并接下来演出其中的主角。后来,她还排演过外国剧《锁着的箱子》、曹禺的《家》、于伶的《女子公寓》、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等,一直到上世纪50年代后,成为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的名教授、莎士比亚专家;翻译出版有《莎士比亚研究》《莎剧解读》等专书。
1937年,当上海租界沦为“孤岛”时,张可与共产党员、学者王元化结识,并一起参与共产党在上海文艺界的组织工作。1938年,锦衣玉食家境里长大的张可加入了共产党,从此将自己的命运,和她的爱人、理想,义无反顾地编织在了一起。1948年后,《展望》杂志被查封。受王元化编辑《地下文萃》的影响,张可怀着儿子到处东躲西藏,躲避国民党的大搜捕,受尽惊吓,却冒着生命危险帮助丈夫。
1949年,儿子王承义与新中国一起,来到张可的生活里。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开始。次年,上海所有的地下党员重新登记,经历了生死洗礼的功臣们,将得以由此进入各级领导岗位。已有12年党龄的张可,却没有前去登记,自动放弃了党籍。张可从没想要从12年的党龄里得到什么回报。她去做了一名大学老师,在并不热闹的莎士比亚研究中,开始了她的人生新旅。
1955年因胡风冤案牵涉,王元化被隔离审查;其间精神严重创伤,靠张可精心照料调养,多方求医问药。元化康复后,她与他一起全心力投入莎士比亚研究,在60年代即完成十多万言的译著。在艰难岁月,她不仅支撑着一个弱小家庭的生存,而且支持着一个人文学者的坚守,支持着文明与文化的基本价值。相夫、教子、敬老,以妇道守人道;译莎评、编刊物、教学生,以文明驱野蛮。没有一句怨语,没有一点倦意,没有一丝放弃。劫难过后,他们的坚守赢来学界文坛有口皆碑的赞誉。王元化有一段质朴深情的文字称赞妻子:
“张可心里几乎不懂得恨。我没有一次看见她以疾颜厉色的态度待人,也没有一次听见过她用强烈的字眼说话。她总是那样温良、谦和、宽厚。从反胡风到她得病前的 23年漫长岁月里,我的坎坷命运给她带来无穷伤害,她都默默忍受了。受过屈辱的人会变得敏感,对于任何一个不易觉察的埋怨眼神,一种稍稍表示不满的脸色都会感应到。但她始终没有这种情绪的流露。这不是任何因丈夫牵连而遭受磨难的妻子都能做到的。因为她无法依靠思想和意志的力量来强制自然迸发的感情,只有听凭善良天性的指引才能臻于这种超凡绝尘之境。”
“文革”中,张可也遭非法隔离。当时她身患高血压症昏厥,不准看病,从此种下病根。1979年6月,张可开会时突发脑血栓,昏迷七日不醒。后来虽经抢救,生命无碍,但思维与脑力严重受损,从此只有简单的言语表达,而读写俱废。她中风的日子,是中国知识人由劫难而复苏的日子,在长冬酷寒的岁月,张可以她的坚韧、仁爱、悲悯与苦难担当精神,渡尽劫波;而大地回春之时,她却再不参加讨论、发表任何意见,寂然淡出历史。
她不参与历史了么?毋宁说,她向历史的造孽出示了受害人无声的审判。
60年代,她常给儿子讲狄更斯《孤星血泪》、《雾都孤儿》、《匹克威尔外传》,以及莎士比亚的《理查德三世》,崇尚19世纪文学传统的人性人情。
张可也教儿子从小读《论语》、《中庸》等经典,又曾以娟秀小楷抄录丈夫有关《文心雕龙》、龚自珍等的专著论文,对中国文化有深厚感情。
诗圣杜甫有一首传诵不衰的名诗:“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润物细无声,正是中国文化的仁爱精神。在张可的身上,洋溢着这种精神。
张可走的那天,远在海外、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史的著名学者林毓生教授寄来挽联,把她比为古代的采莲人:
嵚巇一生、夷然一心,立身不系一丝尘;
音徽如昨、华笺如新,望乡每悼涉江人。
张可王元化传奇故事。
我们的这个长故事,就是开始在这个如今是如此时髦的年代里。 一个在清华园受西式教育长大,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十八岁时成为上海地下党的青年,在上海遇到一个出生在开明富裕的书香世家,祖上在北洋政府任职,非常美丽的,十六岁就考进上海暨南大学,师从郑振铎,李健吾学习英国文学的女孩子。
那个壮怀激烈的湖北籍青年,放弃了在清华大学做教授的父亲为自己设计的留洋计划,在上海参加学生救亡运动,继而带着基督教终身的影响投身中国解放事业,一九三八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出入上海文化界的革命者,就是王元化。他在那个年代,写下了许多关于文艺理论方面的论文,写小说,并负责了共产党在上海文艺界的组织工作,是一个总是有火热的正直与奔突的才情的人。那时的王元化,左倾而且激进,虽然他不能改变自小养成的轻声吃饭的习惯,可他常常穿的裤子像卓别林,他气味相投的好朋友满涛,则每次把家里烫好的衣裤用手揉皱再穿。
那个完美无缺的苏州籍女孩,那个在兄长满涛和他的革命者朋友影响下,在锦衣玉食的自由家庭的包容下,十八岁就参加上海地下党,同年指明自己是一个“温情主义者”的一九三八年的共产党员,就是张可。她在那个年代,翻译奥尼尔的作品,参加了『家』的演出,她演了『早点前』的罗兰夫人,也演了梅表姐,那时她真的是一个美好的女孩子,仁慈而智慧,正直而绝尘,被许多青年追求。直到半个多世纪过去,她年轻时代的照片偶然被两个华东师大的博士生看见,那两个青年蹲在导师王元化的书橱前,感慨照片上那个女子的一派冰雪洁净,那时王元化已经经历了整整二十三年的贱民生涯,他的许多老朋友因为受不住而西归,包括七窍流血而死的挚友满涛,疯狂以后蹈水而死的巴人,众叛亲离,在癌病房孤独死去的顾准。王元化精神危机引起两次心因性的精神失常,一次营养严重不良引起肝炎,一次眼底出血引起失明,那两个博士生握着张可的相片,还是羡慕导师,对导师说:“现在到哪里去找这样的女孩子。”
我们的故事里,王元化得到了张可。
一九三八年,王元化说他喜欢张可,可当时张可不喜欢听到这样的话,质问王元化说这种话是什么意思。 一九四七年,张可的一个追求者问张可她到底喜欢谁,张可此时坦然回答:“王元化。”
一九四八年,王元化和张可在上海慕尔堂举行基督教仪式婚礼。
当时,张可的父亲并不以为王元化是那些候选青年里最出众的,而且在国民党即将大败的前夕,王元化正负责着共产党的地下刊物『地下文萃』,处境非常危险。可是他们没有真正阻止女儿,而是从自己那安适的家里,郑重地把一身白色礼服的美丽女儿带到西藏路上朴素的,带有回廊的教堂里,那里为婚礼装点起白色鲜花,按照张可的心愿,把她的手交到王元化的手上。在那里,这对新人发誓不论生病还是健康,灾难还是幸福,都始终如一,不离开对方直到生命结束。尔后,他们在当时上海甚为豪华的派克饭店(今国际饭店〕度过新婚之夜,从此,共产党员的张可将自己一生的命运和共产党员的王元化联系在一起,开始到处躲藏国民党的大搜捕。
那时被后来的人称为黎明前的黑暗,国民党开始了疯狂的屠杀。上海地下党的李白被杀,蒋介石秘书陈布雷那成为地下党的女儿也不能幸免,就是十里香风,百乐门里彻夜响彻着美国爵士乐的上海,都无法冲去那一年的血腥之气。许多人没有看到自己为之奋斗的新中国到来,就撒手西去。
张可看到了这一天。新中国和她唯一的儿子王承义在一九四九年一起来到她的生活里。
第二年,上海所有的地下党重新登记,准备进入各个领导岗位。张可没有前去登记,自动放弃了经过腥风血雨十二年的党籍。一九三八年她穿着刚烫得平平整整的裙子参加共产党的时候,不是为了吃饭,不是为了逃避买卖婚姻,也不是为了跟赤色的爱人在一起,更不是为了出人头地,她是为了一个在心目中自由,富强的中国,为了一个从书本展现出来的理想。她没想要从十二年的党龄里得到什么物质的好处,她从来不缺,也从不热衷。
她去做了一个教莎士比亚的大学戏文老师,她娴熟的英文和治学的认真,使她成为中国的莎士比亚专家。同时,她也是一个恪尽温柔,相夫教子的主妇,再不用东藏西躲以后,她最喜欢的,是烧许多好吃的菜,开亮客厅每一盏灯,请人吃饭,用最细致的盘子装上她拿手的意大利茄汁面条,俄国浓汤,葡国鸡,擦亮每一副餐具。许多年以后尘埃落定,在她家吃过饭的人回忆起来的,总有她温润的笑容。那些客人里面,有胡风。王元化当时参加筹建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两本书。张可在胡风离开以后,曾表示自己不那么喜欢胡风,因为他太飞扬跋扈。
那个黄金的五十年代,许多年轻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共产党员意气风发,包括王元化,他那楚人血脉里的傲岸,激情与才学,加上新中国的一路慷慨高歌,使得他看上去锐不可当。当时和他共事的李子云,说那时候她都不愿意理她的领导王元化。过了四十年,已经成为王元化患难之交的李子云回忆起来,仍旧在一杯冒着热气的红茶上方大摇其头,坚决地说:“我那时根本不要理他,太‘标’了!”
那时在王元化额头发红,侃侃而谈的时候,张可会看着他,洞悉一切般地笑笑,然后对他竖起修长的拇指来,对他摇晃:“对,对,你总是‘我,我,我’,你是最好的,你不得了。”
一盆温凉的水泼过来了。然后,聪明地不着一词,收兵而去。
静心研究莎士比亚,翻译莎学权威文献,操持一个美好的家,还有对春风得意的亲人狡黠而微讽地竖一竖大拇指头,这是我们这长故事里现在的张可。在她的丈夫王元化和她的哥哥满涛都醉心于契诃夫的时候,她却非常热爱从五四以来就没有在中国热闹过的莎士比亚,而且选择它作为自己终身研究的方向。王元化在七十八岁的时候,还深深记得张可参加地下党那年对自己的评价:一个温情主义者。但他也深深懂得了妻子温情美丽的脸上那稍纵即逝的狡黠笑容,在他气宇轩昂的时候,这是偏安于一隅的张可的品格与智慧,和一个知识妇女的纯净。
到现在,一九五四年了,三十五岁的张可仍旧是一个温情脉脉的人。时髦的三十年代已经远去,张可的故事虽然有些出乎意料,不是程乃珊式的才子佳人,不是蒋光赤式的革命加爱情,不是张爱玲式的岁月磨脏了大小姐,不是徐纡式革命女郎的悲剧,不是杨沫式的脱胎换骨,奔向革命,不是陈学昭式的工作着是美丽的,但她的故事还是以可以想见的方式发展着,你觉得里面有着一种奇特的清爽之气,可我们还不知道这是什么。
五十年代,现在没有想念它的潮流,而张可的故事,却在那时充分地展开了,就象一粒核桃,被砸开了,于是,你才能看到里面淡黄色的果肉。对于张可,要是没有王元化将要开始的二十三年厄运,也没有人知道她的心里开着怎样的花朵。人生它怎么是这样的?要是没有令人不寒而栗的压力,一个人永远也不会知道他的心里藏着怎样的勇气和坚贞。说着张可的故事,看着她优雅地走到了一九五五年六月底,那时她家外面的皋兰路上,高大的梧桐树的树干上褐色的树皮开始爆皮,远远一路看过去,像康定斯基的画,春天又来了。她是一个沉静的女子,可心里一定会对又一个春天的到来有愉快的感觉,那条马路上有一座俄国教堂,退色的莲花式的教堂塔楼在春天薄薄的阳光里像一个感伤的童话故事。张可从那里走过去了,从容的,无辜的。
一九五五年,在全国范围里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胡风运动,株连千人以上。十年以前,王元化已经认识胡风,但交往不多。当时党内已经有人说胡风有严重政治问题,王元化以为缺乏证据。解放初王元化因此一度没有被安排工作。一九五五年六月,王元化忽然被隔离审查,期间周扬提出,王元化是党内少数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造诣较深的学者,如果他肯承认已经公布的关于胡风集团的三批材料属于反革命性质,尽量将他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可被幽禁中的王元化拒绝,即成为胡风反革命分子。
张可完全不知道丈夫的下落,她的家中第一次被抄。她在学校里被人开会逼迫承认丈夫是反革命,被人以书打脸,张可拒绝承认。
一九五七年二月,王元化被释放回家时,已经患上心因性精神病,丧失辨别真假的能力,混淆了现实和幻觉,入睡需要服用安眠药。他的一切都变了,只有他的家一点不曾改变,桌上铺着干净的桌布,衣橱里有熏香,妻子依旧雅致温柔,是他的骄傲。他在家里的习惯不曾改变,他恢复了从前在清华园生活留下的英国人习惯:在床上用托盘吃早餐。要是家里请朋友吃饭,仍旧有意大利茄汁面,葡国鸡和乡下浓汤。 一九五八年,王元化的病情得到缓解,开始找自己喜欢的书来读。当时王元化常常到四马路去看书,虽然那时王元化已经有四年只有少量的生活费,可他还是陆续买了不少书。说起来,这几乎是王元化一生中第一次真正静心读书的时间。他做了许多翻译工作,一方面是他的兴趣,一方面换稿酬来补贴张可的家用。在和他父亲一起译了英国人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以后,开始着手与张可一起翻译莎剧研究文献,并写完『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张可将这近十万字的稿子,用娟秀的毛笔小楷抄在朵云轩的稿签上,用瓷青纸作封面,线装成一册。这悄悄保留着自娱的独版书,后被自己烧毁于文革初期。还完成了论文『秦腔赵氏孤儿』。
时隔三十九年,我看到了抄在五十年代笨拙结实的红色笔记本上的『莎士比亚研究』,张可翻译的大部分,王元化做了全书的润色和校阅,并写了五篇译文题记。这是他们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真正的合作。外面在反右,在全国性的三年自然灾害,没有思想的空间也没有鸡蛋,因为这些翻译的文献完全不可能出版,所以他们把它抄写在两大册笔记本上,每一页都尽量工整地标出了阿拉伯数字的页码,就像一本真正的书一样。那天傍晚,谈起了这两本笔记本的故事,王元化说:“和张可一同在莎士比亚的艺术世界里遨游的日子,是我们一生中美好的回忆。”在没有思想也没有鸡蛋的日子里,他们共同创造了一流的精神生活。
由于极度缺乏营养,王元化得了肝炎,由于张可和家里人一起四下张罗到了足够的黄豆,鸡蛋和食糖,使他一个月身体就完全恢复,可以继续读书和翻译。并常常督促他自己下馆子改善营养。而后王元化的眼睛因病突然失明,那时正是他写作『文心雕龙创作论』的高潮,张可为他找来了上海最好的眼科医生,他八十岁的老父天天步行来,为失明的儿子阅读资料,笔录口述,有八大本之多。
李子云曾说,要不是王元化经历了五十年代的那场坎坷,退守于一个清一色知识分子的温暖家中,他不会成为现在这样的一个中西并进的大学者。
现在,这两本笨拙而结实的笔记本将要被出版,笔记本也将送往上海图书馆被名人手稿室收藏,而张可已经于二十年前中风,抢救过来以后,完全丧失阅读能力。她看不懂她在无望的日子里与丈夫愉快地翻译过的书了。
我想起了张贤亮的『牧马人』,那个纯朴的红衣女子以她的大白馒头和爱情拯救了一个读书人。许多人非常感动于这一点。而张可,则悉心地看顾了王元化的身体,灵魂,以及整个精神世界,她不光拿来了鸡蛋,还拿来了莎士比亚的广阔的智慧的世界。王元化在他的家里,从来不是偶像,也从来不是贱民,他是一个有着恰如其分的尊严的学者。他仍旧保持着他的生活方式,冬天插梅,喜爱鲜花,虽然面有晦色,可穿戴得体。有很长一个时期,敏感的王元化几乎断绝了所有朋友的往来,可是,他的精神上并不十分寂寞,他有张可。
那时张可仍旧常常参加学校的外事活动。六十年代时,来了外国人在上海是希罕事,上海女子的内心不能改变对外国人的好奇和好感,总喜欢多看他们两眼,因为他们来自于一个更华丽的神秘世界。而戏剧学院的女职员们放下手里的工作要多看两眼的,并不是来访的外国人,而是陪同他们的张可老师,那个优雅的,美丽的,从容的女子。她们隐隐知道她的家庭很不幸,可她们在她身上看不到局促和苦楚。以她一贯的低调,这似乎并不是对自尊的保护,更像是她并没有十分耿耿于怀她丈夫地位的变化,也许她会以为两个人在一起翻译莎学的日子是美好的,带着另一种自由的气息。
一个温情主义者并不是没有思想锋芒的人,她亦可以是浮摇于绿色污水中的不沉的莲花。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王元化被打成历史,现行反革命。
一九七零年至一九七二年,再次被隔离审查。离开家庭以后,王元化的心因性精神病复发,比一九五五年的那一次更重。他在奉贤农场里的田野里狂走,在一条不知名的小河滩上看到了一些螃蟹,亦举石悉数砸烂,以驱赶心中的不平和痛苦。失眠症日益严重。
这期间张可因是王元化夫人也被非法隔离,连因高血压晕厥也不准看病,落下严重的病根,导致一九七九年的严重中风,此后读写俱废。
那是更加漫长的艰难时世,看上去没有尽头。我那时是个小孩,不认识王元化一家,也生长在一个由学生向往革命而成为老共产党员的家庭,我的父亲也有严重的失眠症,和王元化看病的是同一家医院,同一些医生,大概也是吃的同一些安眠药,老式安眠药损坏肝脏尤甚。在“文化大革命”中,父亲也是去的奉贤干校。我父亲养猪,常常穿着黑色的高筒套鞋,因为靠着海滩的地方是潮湿的。父亲在干校最痛苦的是集体宿舍不能安静,一旦被同屋吵醒,又不能吃过量的安眠药,就一夜夜的静待天亮。记得每个月他们从干校回家休假的那几天,总是有一辆大卡车载他们回家,绿色的卡车屁股上沾满了黄白色的尘土。一些蓝衣人风尘仆仆地高高跳下,我的父亲戴着有檐的布帽子,他取下帽子的时候,我能看见他额头上被帽子勒出来的一道深深的皱纹。
在许多年以后的今年,听王元化简短地说起那些的时候,我想起了父亲的脸,那时王元化头上也会有被帽檐勒出来的皱纹吗?这次蹉跎就是十年,我的整个青少年时代。而对他们来说,是一生中最年富力强的好时光。
我的妈妈也很美,但她很脆弱,她对我和哥哥们说得最多的话,就是:“不要再给你们的爸爸找任何麻烦。”她常常早上没有起床的时候躺着听早间新闻,要是听到一点点指桑骂槐的句子(在那时它们多得不能数),她就把身体向灯下那小小的半导体凑过去,脸上刹那遍布担忧与紧张。妈妈从来不喜欢听新闻,可是她准时听新闻的习惯一直保持到一九八二年。那一年,我父亲离开他的工作岗位成为顾问,妈妈的早上从此只注意天气预报。不知道张可,她是不是在那十年里就像我的妈妈一样?他们比我的父亲,处在更加险恶的地方。
我们家,从此不再有花了。
听李子云说,王元化的少数几个好友去他家的时候,还是能看到张可温情而清爽的笑容,还是能吃到很正式地用大盘子装了上桌的意大利红烩面,口味纯正,只是少了忌司一样。新年的时候,他们家里还供着清香彻骨的梅花。在某个秘密的灰尘滚滚的角落里,还保藏着泰纳『莎士比亚论』的译文。王元化那被钱谷融称为“像梵高一样的”眼睛,更多地闪耀着真挚和爱情。
没有人知道--甚至是王元化本人--张可付出过多少,才得到这一小块诺亚方舟。
王元化说:“他是仁慈的,超凡脱俗的。”
我们的这个长故事说到这里,那个六十年以前出演奥尼尔笔下小市民的罗兰夫人的美丽女子,仍旧是一个冰雪洁净的人。富裕的生活,得意的生活,愁苦的生活,屈辱的生活,什么都没能使她的心灵变质。她独立在上海的漫长生活中所有能使她变脏的东西之上,成为一个人格优美的莎士比亚专家,现在要是说起中国的莎学研究,人们还是不得不提起张可的名字。
如今,那个美丽的智慧的女子头发雪白,不能读,也不能写,我甚至无法和她深入地交谈,只是她端坐在那里,仍然散发着清凉的洁净的气息。我们其实并不知道真正的三十年代的上海是怎么回事,它是一颗阳光下的钻石,每一面都散发着不同的光华,被不同角度的眼睛看到。要是三十年代像音乐人所说的一样,她真的是受惠于那个时代的人。那个细长手指上的皱纹像菊花的花瓣一样多的老太太,就是张可。
那个才情激昂的青年变得儒雅了,他说他有五十年的时间没有真正像他想的那样做学问,现在他感到自己上了轨道。他的书一本一本地出版了,他去书店签名售新书,那本来不是严肃的学问家的擅长,可人潮滚动。他因为学问的精深和仍能不断吸收与开拓,赢得了几代学人的尊敬。那个思路至今清晰奔放,可胜过他的年轻弟子,身上散发这老人身上难得闻到的淡淡清香的老先生,就是王元化。
当他们相对的时候,他们的眼睛里还是闪烁着活生生的,热热的爱情。
这个长故事里有太多的苦难和坎坷了,我说。
“基督教的说法是,人生就是一个苦难的过程。”王元化说。
“夸张了。”张可说。
与之相关,余秋雨《长者》一文曾提起。
张可个人资料的介绍就聊到这里吧,感谢你花时间阅读本站内容,更多关于张可个人资料图片、张可个人资料的信息您可以在本站进行搜索查找阅读喔。
②文章观点仅代表原作者本人不代表本站立场,并不完全代表本站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③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部分转载文章仅为传播更多信息、受益服务用户之目的,如信息标记有误,请联系站长修正。
④本站一律禁止以任何方式发布或转载任何违法违规的相关信息,如发现本站上有涉嫌侵权/违规及任何不妥的内容,请第一时间反馈。发送邮件到 88667178@qq.com,经核实立即修正或删除。